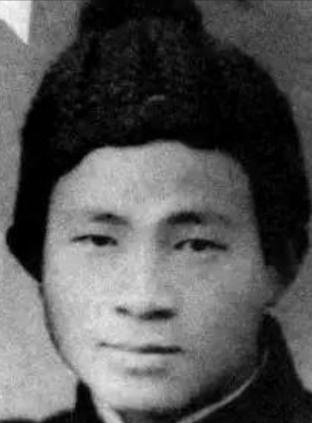1941年,一个男孩在上厕所时,发现墙缝里似乎藏着什么东西,他用手把泥巴刮开,竟然发现了一个油布包,当他打开包裹时,里面的东西让他既害怕又愤怒。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,有这么一个不起眼的油布包。它静静躺在防弹玻璃展柜中,隔绝了外界的喧嚣。 可就是这个包裹,曾经被深藏于寺庙墙缝,又被秘密转移到佛像底座,最终成了审判日本战犯的“京字第一号”铁证,甚至在201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《世界记忆名录》,这本斑驳的相册,封面手绘的血刀图案虽已褪色,却依然刺眼。 故事要从1937年12月的南京说起。那时的南京城,枪声和哭喊声盖过了一切,简直就是人间地狱。城里有个叫罗瑾的15岁少年,在一家照相馆当学徒。他的工作本是冲洗些家长里短的照片,可几个日本兵的闯入,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。 他们得意洋洋地丢下两卷“樱花牌”胶卷,要求冲洗。大概他们也想不到,自己炫耀“战功”的工具,转眼就会变成审判自己的铁证。 暗房里,随着影像在药水中一点点浮现,罗瑾的胃也跟着翻江倒海。照片上不是什么战地风光,而是日军屠杀平民、奸淫妇女的场面。强忍着恐惧和恶心,这个少年做了一个决定:他要偷偷多印一套。 他挑出其中最清晰的16张,做成一本小相册,封面上画了一把滴血的刺刀和一颗流血的心,重重写下一个“耻”字。这本相册,就这么被他藏在了床板底下,成了一个随时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的秘密。 这样的秘密藏不了太久。1941年,汪伪政府的警卫旅进驻毗卢寺,在城里大搞清查。罗瑾心里发毛,觉得床板底下再也不安全。他用油布把相册裹得严严实实,趁着夜色摸到毗卢寺后院的厕所,把它塞进墙缝,又用新泥糊好。 几天后,他提心吊胆地回去查看,却发现墙缝空了,相册不翼而飞。罗瑾当时吓得魂飞魄散,以为是东窗事发,连夜逃回了福建老家。在他看来,这本用命换来的相册,就这么没了,可他不知道,就在他绝望离开的同时,另一双手接过了这份沉甸甸的使命。 一个叫吴连凯(后改名吴璇)的青年正在这里参加汪伪政府的通讯集训。他在后院厕所方便时,无意中发现了墙上那块新抹的泥巴。 出于好奇,他抠开了泥块,那个油布包就掉了出来。打开相册的一瞬间,吴璇也被里面的画面惊得说不出话。他立刻明白,这东西是日军暴行的铁证,必须保护好。 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却难如登天。集训队里,日本教官和特务的眼睛无处不在,私藏这玩意儿,跟玩火没什么两样。吴璇想来想去,把目光投向了大殿里那尊金身弥勒佛像。 在一个深夜,他利用站岗的机会,悄悄将相册藏进了佛像的底座。此后的几年,吴璇就守着这个秘密,佛像底座下的相册,成了他心头最大的牵挂。 直到1945年8月,日本投降。南京军事法庭成立,开始向社会公开征集日军罪证。吴璇毫不犹豫,将这本守护了多年的相册交了出去。经过鉴定,法庭确认照片真实有效,并将其列为“京字第一号”证据。 在审判谷寿夫等战犯时,这些照片成了无法辩驳的铁证,将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送上了断头台。而在相册的最后一页,人们发现了罗瑾当年用铅笔写下的一行字:“若有人问起,就说是一个中国人留下的。” 罗瑾和吴璇,两个此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,因为这本相册,在法庭的走廊上有过一次短暂的交集。他们没有说太多话,只是紧紧握了握手,一切尽在不言中。直到1995年,抗战胜利50周年,两位都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才再次重逢。 此时的罗瑾,右耳因当年被日本兵殴打早已失聪;吴璇的背也驼了。面对这本相册的复印件,他们一页页地烧给逝去的同胞,算是迟到了几十年的告慰。 有人问他们当年怕不怕。罗瑾坦言,怎么可能不怕,但留下证据,就是为了让日本人血债血偿。吴璇也说,怕是肯定的,但有些事必须有人做,如果证据没了,那些人就真的白死了。 2014年,首个国家公祭日,两人的后代将这本相册原件正式捐赠给纪念馆。如今,它静静地躺在那里,展柜旁的说明牌上写着:“由普通市民罗瑾、吴璇冒死保存”。 每天,无数参观者在它面前驻足,有人鞠躬,甚至有日本老人来到这里深深鞠躬,承认只有正视历史,才能避免悲剧重演。 在当年的那起“南京大屠杀”中,短短的六周时间内,有30万的军民命丧在了日寇的屠刀之下,如此暴烈的恶行,放眼整个人类的历史,也是绝无仅有的,我们也要永远牢记这段悲痛的历史,发奋自强,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,壮大自己的力量,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。 信源:抗日战争纪念网2020.5.20一本滴血的相册